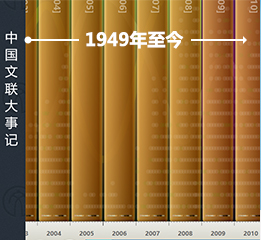《歲月碎裂的聲音》
張杰 著
知識(shí)出版社出版
張杰是個(gè)不合時(shí)宜的人。無(wú)論于他黃河岸邊的老家,還是他后來(lái)流浪的城市。
張杰是個(gè)以夢(mèng)為馬的人。一匹童話里的木馬,或類似唐吉訶德那樣的坐騎。他愛(ài)上的東西太多,由此衍生了無(wú)數(shù)的責(zé)任、意義、承諾、榮譽(yù)感和使命感,使得他生命的行李過(guò)重。同時(shí),他愛(ài)的東西太特殊,在傳說(shuō)中和史書(shū)上都太顯赫、太有尊嚴(yán)和光環(huán),這增加了他的生存幻覺(jué)。
其實(shí),這些常人眼里的“荒誕”,都是純粹藝術(shù)家的典型特征。換一棟時(shí)空,比如19世紀(jì)的俄羅斯莊園,文藝復(fù)興和啟蒙時(shí)代的歐洲沙龍,甚至上世紀(jì)80年代理想主義的中國(guó),張杰會(huì)如魚(yú)得水,如燕穿梭。
張杰寫(xiě)過(guò)一篇《植物》,我覺(jué)得作為他的自畫(huà)像是很合適的。
“我至今清晰記得一種類似高粱的高桿作物,它們被種植在密密而低矮的大豆或爬行植物中間,看上去更像是一種田野守護(hù)者。而這是一些幾乎沒(méi)有任何食用價(jià)值的作物……它們高傲地站在那些低矮的爬行植物中,是田間最后的勝利者和惟一靠尊嚴(yán)活著的族群。我在詞典里沒(méi)有找到它們的名字。”
這種英雄主義式的悲情,是張杰胸腔里的手風(fēng)琴發(fā)出的。我見(jiàn)過(guò)他描述的這種植物,紅色的籽粒,美艷驚人卻泛著苦難的光澤,高高瘦瘦的身?xiàng)U,很像唐吉訶德。整體上說(shuō),那是一種氣質(zhì)孤獨(dú)、高尚而瀕臨絕跡的植物。
不僅農(nóng)民不種了,甚至還用農(nóng)藥來(lái)對(duì)付它。因?yàn)樗粚?shí)用。
我一直想,若張杰不癡愛(ài)文學(xué),或愛(ài)上卻不獻(xiàn)身,會(huì)怎樣?會(huì)過(guò)一種怎樣的生活?
其實(shí),我很希望他開(kāi)一家唱片店或樂(lè)器行,小小的,不賠不賺的那種,在一條隱蔽的巷子里,很靜,很深,門(mén)口或屋后有棵大樹(shù),樹(shù)上有鳥(niǎo)。這樣,我會(huì)常在一個(gè)懶洋洋的午后或傍晚去找他,聽(tīng)他新刻的唱片,聽(tīng)他語(yǔ)焉不詳?shù)剜洁焓裁础蚁耄以撌遣叫谢虻泡v破自行車去。
這個(gè)城不能太大,不能大到讓朋友在街上永無(wú)撞懷的可能,不能大到讓人輕易地失蹤和杳無(wú)音信。這個(gè)城應(yīng)有這樣的特征:空氣柔軟,人群、光影、風(fēng)速緩慢移動(dòng),不焦灼,不激烈,且慷慨大度,能收容大量游手好閑和胡思亂想的人,尤其像張杰這樣羞澀而簡(jiǎn)單的人,應(yīng)支持他這種人和人生。不應(yīng)太刁難他們,不應(yīng)給其出太多的難題。
可惜,心愿落空了。中國(guó)沒(méi)有這樣的城了。這樣的城太文弱,禁不住鏟車輕輕一推,經(jīng)不起人們發(fā)財(cái)夢(mèng)想的起哄和抗議。同時(shí),張杰也退不回他魯西南的故鄉(xiāng)了,光禿禿的村莊,在那里,池塘被埋,樹(shù)林被伐,到處是尋找人民幣的刀光劍影。沒(méi)有詩(shī)歌,更沒(méi)有音樂(lè),只有貧寒、茫然、牢騷、被剝削的憤怒、唉聲嘆氣和自相殘殺,他會(huì)顯得更加突兀、刺眼。在那里,他只會(huì)更加哀愁、憂郁,他會(huì)像老人一樣,只能聽(tīng)見(jiàn)自己的咳嗽,整日盯著影子發(fā)呆。
他只能不停地走。鄄城,濟(jì)南,廣州……
相隔大約10年后,我們?cè)诒本┮?jiàn)了面。
這個(gè)城市一點(diǎn)不支持他的活法。像做錯(cuò)事的小學(xué)生,他羞愧地把音樂(lè)和詩(shī)歌裝進(jìn)了書(shū)包,雙手捂住,然后按報(bào)社的吩咐,拿著筆和采訪本天天跑,跑得他都說(shuō)不清自己在哪里。
每當(dāng)他開(kāi)始為生計(jì)奔波并汗流浹背、焦頭爛額的時(shí)候,我總有一種印象:時(shí)代在非法使用“童工”。
張杰有兩個(gè)貴族般的嗜好:音樂(lè)和詩(shī)歌。在我看來(lái),他的音樂(lè)天賦高于詩(shī)歌。從耳朵到神經(jīng)到心靈,他的音樂(lè)器官都是一流的。我有個(gè)酷愛(ài)古典音樂(lè)的朋友,她本人已有很多音樂(lè)家知音,但和張杰僅僅聊了一會(huì),即驚訝他的音樂(lè)體驗(yàn),后來(lái)又迷上他私自制作的CD。她說(shuō),張杰制作的CD水平遠(yuǎn)超過(guò)幾百元一張的市場(chǎng)貨。
一個(gè)從玉米地逃出來(lái)的人,竟然對(duì)唱片和器材有這么深的領(lǐng)悟和心得。這不是天才是什么?這不是流亡貴族的基因么?
音樂(lè)對(duì)他有多重要?他居然敢給兒子起名叫巴赫!張巴赫!
讓我想想,我是怎么認(rèn)識(shí)張巴赫之父的?
文學(xué)。是文學(xué)制造的偶然。多年前,我在山東,一位我們共同敬重的作家朋友帶他去我的城市。飯桌上,他掏出一個(gè)小包,裝著從黃河岸邊的老家?guī)?lái)的油炸“爬蟬”,這是我至今懷念的美味。然后就是徹夜長(zhǎng)談,那時(shí)的夜真長(zhǎng)啊,能聊無(wú)數(shù)的東西,無(wú)數(shù)的遠(yuǎn)方,無(wú)數(shù)的人,無(wú)窮的時(shí)代……那時(shí)候,文學(xué)是心靈愛(ài)好者之間的密碼,猶如精神通行證,有了它,彼此交往上可省略很多東西。我們就這樣省略了很多東西,直接成了朋友。那種即使多年未遇也不覺(jué)得遠(yuǎn)離的朋友。
我一直覺(jué)得,像張杰這樣容易迷路的人,不該居住在大城市,甚至不該是城市。他應(yīng)該住在一個(gè)溫柔的小地方。可如今的中國(guó),連村莊都消滅了溫柔,都被粗野和狂熱所占領(lǐng),他該去哪兒呢?
他屬于“小”,即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家舒馬赫贊美的那種“小即美”的小。他是一個(gè)熱愛(ài)細(xì)微的人,一個(gè)內(nèi)心有明珠、不宜曝曬、需要幽閉的人,像蚌,像螢蟲(chóng)。可這樣的物種,越來(lái)越少,供之躲藏的河塘和草叢都蒸發(fā)了。
他只有上岸。向“大”屈服,在“大”里尋找角落和洞穴。
精神上,張杰有三個(gè)身份:音樂(lè)狂、作家或詩(shī)人、基督徒。這三個(gè)身份都和信仰有關(guān),都被他提升到了和生命等值的層面。通常,一個(gè)人有其一就夠受的了,即足以和人群拉開(kāi)距離,顯得孤單和怪異。他居然有仨,真讓人羨慕又同情。這意味著,他要同時(shí)聽(tīng)從這三個(gè)領(lǐng)域的召喚和指令,既享受她們,又服侍她們,遵循她們的原則和尺度,聽(tīng)從她們的吩咐和調(diào)遣……
這注定了他活不輕松。他的心路全是幽徑、叢林和峽谷。雖然美,但障礙多,體力消耗大。
我最羨慕的是他第一個(gè)身份。第二個(gè)身份,我本人兼有,所以不怎么看重。但第二個(gè)身份害了我,因?yàn)閺埥芤鰰?shū)了,張杰吩咐我為他的書(shū)寫(xiě)點(diǎn)什么。我就想,我要是不會(huì)寫(xiě)東西就好了。我已好久不寫(xiě)東西了,尤其序或評(píng)之類,我壓根不會(huì)寫(xiě)。
但這是必須的,是來(lái)自友情的指令。
這本書(shū)里,我最愛(ài)讀的是他的鄉(xiāng)村紀(jì)事,尤其和他兒子有關(guān)的事。讀的時(shí)候,我總想笑,又總想哭,總?cè)滩蛔∧畛雎晛?lái)。
“回到小縣城里找一個(gè)地方吃飯,把自己灌醉,然后下午去看城西那些尚未盛開(kāi)的桃花……張巴赫和我的收獲是撿拾了一些剪枝人剪在地下的花枝,回去插在水里,第二天居然開(kāi)了很多。”(張杰《黃河咫尺桃花》)
這對(duì)父子是故鄉(xiāng)桃花的唯一審美者。我感動(dòng)于父子的孤獨(dú)和勇氣,大白天,別人都在勞作,他們竟然把自己打扮成知音的模樣,醉醺醺、赤裸裸去拜訪桃花,竟然認(rèn)為花朵比果實(shí)重要。這就是詩(shī)人,他給了兒子一個(gè)春天的儀式,他露骨的好色,不怕被村莊嘲笑。
我一直覺(jué)得,好的敘事風(fēng)格,無(wú)論小說(shuō)還是散文,都應(yīng)是自由、流暢、松弛的,猶如野外散步,沒(méi)有路,即遍地是路了。張杰有許多篇什都做到了這一點(diǎn),當(dāng)他不對(duì)寫(xiě)作本身提要求的時(shí)候,他寫(xiě)得最好。
“在我的經(jīng)驗(yàn)里,人的地位似乎與所分到的土地的位置相對(duì)應(yīng)。小時(shí)候家里總是分到一些離村里最遠(yuǎn)的地塊,這除了多花費(fèi)很多勞動(dòng)之外,還意味著受歧視的位置——最差的地塊總是等著那些運(yùn)氣最差的人……那塊地里,我還曾經(jīng)見(jiàn)到過(guò)出產(chǎn)過(guò)幾十斤重的一株地瓜。被視為村里的奇跡。”(張杰《不停變換位置的土地》)
簡(jiǎn)明、高效、舉重若輕,充滿童年的純真和陽(yáng)光氣息,充滿宗教的憂郁和正直。在張杰作品中,我最喜愛(ài)的即這類無(wú)意中包含詩(shī)意的寫(xiě)實(shí)和紀(jì)事。
我甚至隱約覺(jué)得,若有足夠耐心和不被干擾的環(huán)境,張杰或許能寫(xiě)出像契訶夫那樣的東西。讀《鄄城和黃河之間的村莊》系列時(shí),我就想起了契訶夫的《草原》,它們有相似的氣息。
“這個(gè)叫做桑莊的村子里的人率先集體做起樹(shù)木生意,此前這個(gè)村莊周圍曾被桑樹(shù)環(huán)抱,村莊因此而得名。周圍的樹(shù)木曾在默認(rèn)里被一陣陣蠶食的聲音所吞沒(méi)。村莊曾在這種沙沙聲幸福如雨,即使最大的鼾聲也無(wú)法穿透厚厚層層的墨黑樹(shù)葉……而且我知道,痛苦來(lái)自被我們賣掉的樹(shù)木和村莊。”
痛苦來(lái)自被賣掉的樹(shù)木和村莊。
其實(shí),這也是張杰退不回去的原因。他只能以逃離的方式親近故鄉(xiāng),以背叛的姿態(tài)熱愛(ài)村莊,熱愛(ài)他記憶中的黃河和桃花。
“村里一共有四個(gè)池塘,轉(zhuǎn)眼間,四個(gè)池塘枯了三個(gè),村后、村西和村前的三個(gè)先后干涸,村后的那個(gè)上面蓋了房子……池塘們好像說(shuō)好了一樣,一起干枯或走向干枯。”(《這片池塘還剩下什么》)
干枯。像說(shuō)好了一樣,事物一起走向干枯。
黃河枯了。鄉(xiāng)村枯了。城市,早已枯了。
張杰在干枯的洼里地晃動(dòng),像個(gè)失業(yè)的青蛙。
他依舊在唱、在鳴,那或許叫音樂(lè),叫詩(shī)歌,也或許叫哭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