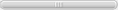吳天明重回黃土地再刮西北風(fēng)

吳天明(右)執(zhí)導(dǎo)電影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
吳天明已經(jīng)離開(kāi)黃土地太久。
1986年,36歲的攝影師張藝謀被47歲的導(dǎo)演吳天明相中,成了電影《老井》的男主角孫旺泉。在老井村一望無(wú)際的黃土高坡上,黝黑干瘦而又目光執(zhí)著的張藝謀一鎬一鎬地刨著干硬的土地,在他身旁不遠(yuǎn)處,隱藏于那臺(tái)轉(zhuǎn)動(dòng)不停的攝影機(jī)之后的矮胖男人,就是當(dāng)時(shí)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廠長(zhǎng)吳天明。
在那部被譽(yù)為“第四代”導(dǎo)演巔峰之作的《老井》過(guò)后,吳天明廣為人知的影片僅有講述川劇藝人的《變臉》一部,黃沙漫天的西部高原似乎已與西北漢子吳天明的視野漸行漸遠(yuǎn)。2012年6月,吳天明終于決定再度開(kāi)拍扎根西北的電影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。這部影片講述的是在社會(huì)變革的年代里,新老兩代陜西嗩吶藝人為了信念的堅(jiān)守所產(chǎn)生的真摯師徒情、父子情以及兄弟情。“我希望能找到當(dāng)年拍攝《人生》《老井》時(shí)的那種感覺(jué)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。
導(dǎo)演吳天明:
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是我的感懷言志之作
提起吳天明,不能繞過(guò)的兩部作品就是《人生》和《老井》。1982年,作家路遙發(fā)表在《收獲》雜志上的中篇小說(shuō)《人生》,引發(fā)了全國(guó)范圍的熱烈討論,兩年之后,吳天明便將小說(shuō)搬上大銀幕,影片所塑造的男主人公高加林,儼然成為一代知識(shí)分子的縮影。又過(guò)了兩年,吳天明拍攝出蘊(yùn)藏著中華民族精神力量的寓言式影片《老井》,從知識(shí)分子史詩(shī)跨越到普世性更為廣泛的農(nóng)民史詩(shī)。一個(gè)最能代表20世紀(jì)80年代文化界思想解放精神的電影導(dǎo)演,從此橫亙于中國(guó)影史之中。
現(xiàn)在回憶起20多年前的往事,吳天明總是不勝唏噓,感到今天的中國(guó)電影,已經(jīng)讓他這個(gè)73歲的老人看不懂、摸不透。“伊朗電影《納德與西敏:一次別離》成本只有30萬(wàn)美金,藝術(shù)風(fēng)格也質(zhì)樸無(wú)華,但片中人物所體現(xiàn)出的人格與信仰力量,卻贏得了世界的尊敬,在各大電影節(jié)上屢獲大獎(jiǎng)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這與中國(guó)影人動(dòng)輒用千萬(wàn)甚至上億元投資的電影沖擊國(guó)際電影節(jié)卻屢遭失敗,形成了鮮明對(duì)比。中國(guó)電影不缺錢(qián),缺的是創(chuàng)作者對(duì)藝術(shù)的真誠(chéng)、對(duì)生活的熱情以及對(duì)社會(huì)人生的深刻思考。”
賦予電影強(qiáng)烈的社會(huì)意義與巨大的精神力量,是吳天明對(duì)于創(chuàng)作的一貫追求。這一追求,當(dāng)然會(huì)體現(xiàn)在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當(dāng)中。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(shuō),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是我醞釀多年的感懷、言志之作。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夠追求一種精神,堅(jiān)守一種信念,褒揚(yáng)一種人類共有的價(jià)值觀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在時(shí)代大潮轉(zhuǎn)折的過(guò)程中,傳統(tǒng)鄉(xiāng)村社會(huì)原有的禮俗與秩序正在解體;而嗩吶這種民間藝術(shù)形式在現(xiàn)代化的擠壓下,也正在逐漸消亡。我所關(guān)注的,是在這解體與消亡的過(guò)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”
影片的男主角焦三爺由陶澤如飾演,而年輕一代嗩吶藝人游天鳴則由新人李岷城扮演。關(guān)于選角,吳天明坦言自己只選最好的,不選最貴的。“焦三爺是個(gè)外冷內(nèi)熱的老人,看起來(lái)嚴(yán)肅古板,其實(shí)心懷熱血。陶澤如是我心目中最適合這個(gè)角色的演員,他除了能演出嗩吶藝人的堅(jiān)守、固執(zhí),還能演出飄逸、神奇的精氣神來(lái)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現(xiàn)在很多電影唯明星論,不管片中的角色是張三還是李四,都請(qǐng)最火、最大牌的明星來(lái)演。我就納悶了,這世上哪兒來(lái)的那么多萬(wàn)能演員?找最合適的演員演最合適的角色,一向是我的選角標(biāo)準(zhǔn)。拍《老井》的時(shí)候,我不就選擇了當(dāng)時(shí)還是攝影師的張藝謀擔(dān)當(dāng)主演嘛!”
除了演員,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中的音樂(lè)也是吳天明十分關(guān)注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“講述嗩吶藝人的生活,音樂(lè)自然是重中之重。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原本是一首難度超高、只為德高望重之人吹奏的葬禮古曲,這次我們邀請(qǐng)了著名作曲家張大龍深入陜西采風(fēng),選取陜西音樂(lè)素材,創(chuàng)作了一首全新的陜西版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這段曲子作為全片的主題音樂(lè),加上重新創(chuàng)作加工的20多首嗩吶曲,再伴以交響樂(lè)隊(duì)的協(xié)奏,中西合璧,為影片烘托出了一種厚重蒼勁、凄婉動(dòng)人的氣韻之美。”
“伯樂(lè)”吳天明:
大不了扒了我的烏紗帽
在上世紀(jì)80年代的中國(guó)影壇,有句盡人皆知的“行話”:“西望長(zhǎng)安,有個(gè)西影廠;西望長(zhǎng)安,有個(gè)吳天明。”1983年,44歲的吳天明升任西安電影制片廠廠長(zhǎng),成為當(dāng)時(shí)全國(guó)各大電影廠中最年輕的掌門(mén)人。在任的6年里,吳天明除了自己執(zhí)導(dǎo)影片,還在鐘惦棐等老一輩電影人的倡導(dǎo)下扛起了“西部電影”的大旗。在他的率領(lǐng)下,《野山》《老井》《紅高粱》《雙旗鎮(zhèn)刀客》等一大批表現(xiàn)西北大地風(fēng)土民情的優(yōu)秀影片脫穎而出,一股強(qiáng)勁的“西北風(fēng)”令當(dāng)時(shí)的中國(guó)影壇甚至世界影壇感到震驚。張藝謀、周曉文、黃建新、顧長(zhǎng)衛(wèi)等諸多“第五代”精英在創(chuàng)作發(fā)軔期都曾得到過(guò)吳天明的扶持與幫助,“第五代教父”在一段時(shí)期內(nèi)成為吳天明的別號(hào)。
時(shí)過(guò)境遷,吳天明認(rèn)為這個(gè)漸已被人遺忘的別號(hào)根本不值一提。“當(dāng)時(shí)坐在廠長(zhǎng)的位子上,我的任務(wù)就是振興西影廠。怎么振興?靠那些老人肯定不行,只能靠年輕人。我所做的只不過(guò)是把一批有才華的青年電影人請(qǐng)到西影廠,并且盡可能地支持他們拍攝作品。他們中的有些人很爭(zhēng)氣,拍了一些好電影,其結(jié)果是為西影廠爭(zhēng)了光,也為我這個(gè)廠長(zhǎng)爭(zhēng)了光。所以說(shuō),不是人家‘第五代’應(yīng)該感謝我,而是我應(yīng)該感謝人家。至于‘第五代’日后所取得的成績(jī)和產(chǎn)生的好或不好的變化,都跟我沒(méi)半點(diǎn)兒關(guān)系。”吳天明淡然地說(shuō)。
主演《老井》時(shí),做了4年攝影師的張藝謀對(duì)吳天明說(shuō),自己想把莫言的小說(shuō)《紅高粱》拍成電影。吳天明讀過(guò)小說(shuō),很快就同意了這個(gè)攝影師的“非分”之請(qǐng)。張藝謀興高采烈地跑到山東高密,轉(zhuǎn)了一圈后卻發(fā)現(xiàn)莫言小說(shuō)里寫(xiě)的地方壓根兒就沒(méi)有高粱,必須得自己種上,然后秋天再去拍。于是張藝謀回到西影廠,向吳天明打報(bào)告申請(qǐng)資金去種高粱。“依照當(dāng)時(shí)制片廠的程序,必須劇本審過(guò)后,經(jīng)過(guò)廠長(zhǎng)辦公會(huì)議、常務(wù)會(huì)通過(guò),財(cái)務(wù)科才能拿出錢(qián)來(lái),可當(dāng)時(shí)張藝謀連《紅高粱》的劇本都沒(méi)有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我就找到廠里的幾個(gè)車間主任,跟他們湊了4萬(wàn)塊錢(qián),讓張藝謀趕緊去高密種高粱。其實(shí)這是違反常規(guī)的做法,弄不好會(huì)影響我的廠長(zhǎng)之位。但事實(shí)上我并不想當(dāng)官,我心里想的都是怎么讓西影廠繁榮起來(lái),所以就當(dāng)機(jī)立斷地湊了錢(qián)。那時(shí)我想,大不了就把我那小小的烏紗帽給扒嘍。”
在第二屆北京國(guó)際電影節(jié)上,吳天明被授予“中國(guó)電影人伯樂(lè)”獎(jiǎng),但他的獲獎(jiǎng)致辭,卻與自己的獎(jiǎng)項(xiàng)有些相悖:“年輕導(dǎo)演不應(yīng)只把自己的未來(lái)寄托在‘伯樂(lè)’身上,更要將命運(yùn)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只要努力,任何年輕導(dǎo)演都有可能成為真正的‘千里馬’。”
這就是吳天明。他的眼中只有電影,個(gè)人榮譽(yù)不過(guò)是過(guò)眼云煙。
觀察者吳天明:
我就是那個(gè)說(shuō)真話的小孩
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開(kāi)拍前,吳天明還破天荒地主演了兩部電影,兩部電影的導(dǎo)演都是張揚(yáng)。一部是常規(guī)的影院電影《飛越老人院》,一部是時(shí)下最流行的微電影《老人愿》。吳天明說(shuō),演戲?qū)τ谧约憾约兇馐恰巴嫫薄保谘輵虻倪^(guò)程中,自己卻頗有感觸,“我發(fā)現(xiàn)跟我一起演戲的那些老藝術(shù)家有一個(gè)共同特點(diǎn),就是要求都很簡(jiǎn)單。大家從不主動(dòng)要片酬,從來(lái)不要求報(bào)銷,住在墻壁斑駁的招待所里也沒(méi)一個(gè)人有怨言,老人們就是想把戲演好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反觀一些年輕的所謂‘大腕’,不僅沒(méi)高片酬就不演,而且還要求住高檔酒店,到哪兒都是助理、經(jīng)紀(jì)人一大堆,心里卻很少琢磨該怎么詮釋自己所演的人物。”
由演員圈的浮躁,吳天明聯(lián)想到了整個(gè)中國(guó)電影界存在的問(wèn)題。“批量生產(chǎn)的商業(yè)電影固然正在促進(jìn)著中國(guó)電影市場(chǎng)的繁榮,但產(chǎn)業(yè)化10年來(lái)真正具備精神層面追求的國(guó)產(chǎn)商業(yè)片又有幾部?我們總是說(shuō)要學(xué)習(xí)好萊塢,好萊塢最值得我們學(xué)習(xí)的是什么?支撐在很多極具觀賞性的好萊塢商業(yè)片背后的,是一種正面、積極的價(jià)值觀。誠(chéng)信、友情、奮斗等人類共有的價(jià)值追求,無(wú)時(shí)無(wú)刻不從那些優(yōu)秀的商業(yè)電影中滲透出來(lái)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而我們的商業(yè)片呢?在娛樂(lè)過(guò)后,觀眾還能回味什么、還能反思什么?電影是文化產(chǎn)品,承載著傳播人類精神文明的重任。在精神上作假、放棄本民族優(yōu)秀文化傳統(tǒng)、放棄人類共有價(jià)值追求的電影,拍出來(lái)又有什么意義呢?”
1995年,香港邵氏公司找到吳天明,邀請(qǐng)他執(zhí)導(dǎo)一部表現(xiàn)川劇藝人生活的電影。吳天明拿到邵氏提供的劇本,發(fā)現(xiàn)自己面對(duì)的是“一個(gè)十分商業(yè)、而且商業(yè)得非常低級(jí)的故事”。吳天明在刪掉了大量諸如將通奸的女人扒光了綁住的橋段之后,陷入了深深的思索:這部電影究竟應(yīng)該表現(xiàn)什么?這時(shí)北影廠的老導(dǎo)演水華給吳天明提了個(gè)醒:應(yīng)該表現(xiàn)人間的真情。于是按照這個(gè)思路,吳天明完成了電影《變臉》。
“當(dāng)初確定這個(gè)主題,是因?yàn)槲覀兊纳鐣?huì)的確很需要真情。如果當(dāng)時(shí)的我知道在十多年后,我們的社會(huì)上會(huì)出現(xiàn)扶摔倒的老人起來(lái)反被栽贓、學(xué)雷鋒的人被當(dāng)成精神病關(guān)進(jìn)精神病院的‘怪事’,一定會(huì)更加堅(jiān)定自己的信念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一部電影改變不了一個(gè)國(guó)家,也改變不了一個(gè)民族,但作為電影工作者,我們拍攝的每一部電影都應(yīng)該堅(jiān)守一種精神,通過(guò)電影藝術(shù)來(lái)呼喚人與人之間的信任、頌揚(yáng)人世間的真情。”
吳天明向來(lái)喜歡說(shuō)真話,即便說(shuō)真話時(shí)常會(huì)得罪人,而且往往說(shuō)了也白說(shuō),他還是堅(jiān)持要說(shuō)。“白說(shuō)也得說(shuō),發(fā)聲總比沉默好。我到了這把年紀(jì),已經(jīng)無(wú)欲無(wú)求、無(wú)所顧忌了。”吳天明說(shuō),“就像《皇帝的新衣》的故事,明明皇帝光著屁股,可群臣都夸他穿得如何漂亮,只有那個(gè)小孩說(shuō)了真話。如今的我就想做那個(gè)敢于說(shuō)真話的小孩。”
當(dāng)被記者問(wèn)起,以73歲的“高齡”拍攝《百鳥(niǎo)朝鳳》,是否感到有些力不從心時(shí),吳天明半開(kāi)玩笑地回答說(shuō):“沒(méi)半點(diǎn)兒力不從心。只要我還活著,只要還有人愿意給我投資,我就會(huì)一直拍下去。”
(編輯:孫育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