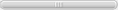大數(shù)據(jù)時(shí)代的藝術(shù)學(xué)對(duì)策研究
2011年2月,國務(wù)院學(xué)位委員會(huì)審議批準(zhǔn)了經(jīng)過調(diào)整的《學(xué)位授予和人才培養(yǎng)學(xué)科目錄》。這個(gè)“學(xué)科目錄”的頒布順應(yīng)了我國藝術(shù)學(xué)界長期的、強(qiáng)烈的訴求,“藝術(shù)學(xué)”由一級(jí)學(xué)科升格為“學(xué)科目錄”中的第13個(gè)學(xué)科門類。當(dāng)時(shí)我曾撰文,認(rèn)為“藝術(shù)學(xué)”的升格主要不是學(xué)理建構(gòu)的效應(yīng)而是學(xué)域擴(kuò)張的影響。我曾指出:對(duì)于藝術(shù)學(xué)的學(xué)理建構(gòu),事關(guān)學(xué)科門類獨(dú)立后的學(xué)科品質(zhì)。藝術(shù)學(xué)各藝術(shù)樣式學(xué)理建構(gòu)的特質(zhì),在于其具有極高藝術(shù)含量的實(shí)踐性。如何將這種“實(shí)踐性”上升為“實(shí)踐理性”,是藝術(shù)學(xué)學(xué)理構(gòu)建的核心課題。兩年過去了,我總覺得藝術(shù)學(xué)學(xué)理建構(gòu)似乎還缺點(diǎn)什么,而這個(gè)所“缺”之“點(diǎn)”不只是在“實(shí)踐性”上升為“實(shí)踐理性”方面顯得薄弱,而且在“學(xué)理性”轉(zhuǎn)化為“學(xué)理對(duì)策”方面顯得極度疲軟。
一、必須正視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“短板”現(xiàn)象
我們所說的藝術(shù)學(xué)“對(duì)策研究”不是藝術(shù)學(xué)“研究對(duì)策”。我在有些學(xué)術(shù)機(jī)構(gòu)做這一講座時(shí),主持人往往會(huì)說成“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對(duì)策”。或許在其潛意識(shí)中感覺到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某種不足,認(rèn)為需要在“對(duì)策”上加以考量。其實(shí),我們所說的“對(duì)策研究”,是對(duì)既往“應(yīng)用研究”或“現(xiàn)狀研究”的一種更具針對(duì)性、更講有效性的表述。
對(duì)一個(gè)事物水準(zhǔn)高低的總體評(píng)價(jià),不在其“高圍”而在其“短板”。盡管多年來藝術(shù)學(xué)學(xué)理建構(gòu)成就斐然,但它在“對(duì)策研究”方面存在著明顯的不足。
1.對(duì)策研究的“短板”在于“問題意識(shí)”的薄弱
我們所說的藝術(shù)學(xué)“對(duì)策研究”不是藝術(shù)學(xué)“研究對(duì)策”。我在有些學(xué)術(shù)機(jī)構(gòu)做這一講座時(shí),主持人往往會(huì)說成“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對(duì)策”。或許在其潛意識(shí)中感覺到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某種不足,認(rèn)為需要在“對(duì)策”上加以考量。其實(shí),我們所說的“對(duì)策研究”,是對(duì)既往“應(yīng)用研究”或“現(xiàn)狀研究”的一種更具針對(duì)性、更講有效性的表述。相比較而言,應(yīng)用研究過于把重心放在基礎(chǔ)研究,強(qiáng)調(diào)的是基礎(chǔ)研究的“應(yīng)用”;而現(xiàn)狀研究則過于把重心放在現(xiàn)狀的描述,不強(qiáng)調(diào)提出“問題”并進(jìn)而提出“對(duì)策”。很顯然,我們較少提“對(duì)策研究”,本身就意味著針對(duì)性“問題意識(shí)”的薄弱,也意味著有效性“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”的缺失。
這可能意味著,我們基礎(chǔ)研究與對(duì)策研究的關(guān)聯(lián)性出現(xiàn)了某種“斷裂”。基礎(chǔ)研究是普遍性的學(xué)理研究,對(duì)策研究是特殊性的學(xué)識(shí)研究;前者是后者的累積與升華,后者是前者的推演與修正。基礎(chǔ)研究與對(duì)策研究關(guān)聯(lián)性的斷裂,可能主要在于“基礎(chǔ)研究”研究程序的“內(nèi)在化”。也就是說,“基礎(chǔ)研究”過于沉迷于純粹的學(xué)理研究,不關(guān)心“對(duì)策”因而也難以在對(duì)策研究中獲取新的“學(xué)識(shí)”。基礎(chǔ)研究與對(duì)策研究的關(guān)聯(lián),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(guān)聯(lián),這個(gè)“關(guān)聯(lián)”的斷裂,在于我淡忘了“普遍性寓于特殊性”這一哲學(xué)命題。基礎(chǔ)研究的學(xué)理,是對(duì)既往眾多“特殊性”的分析與歸納,是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存量;對(duì)策研究的學(xué)識(shí),是在新的“特殊性”面前將既往的“普遍性”加以推演與修正,是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增量。我們當(dāng)前亟須的,是不斷通過增量的“特殊性”學(xué)識(shí)去構(gòu)建存量的“普遍性”學(xué)理。
基礎(chǔ)研究與對(duì)策研究關(guān)聯(lián)性的斷裂,雖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對(duì)策研究的明顯不足,但對(duì)策研究的“短板”使基礎(chǔ)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現(xiàn)出“板短”。基礎(chǔ)研究的“書齋化”與對(duì)策研究的“急就章”是這一“斷裂”必然給雙方都帶來的后果。事實(shí)上,當(dāng)基礎(chǔ)研究沉湎于“本本”之時(shí),也同時(shí)是對(duì)策研究失語于“現(xiàn)象”之際。一方面,是基礎(chǔ)研究的“書齋化”隔絕了“源頭活水”;另一方面,是對(duì)策研究的“急就章”呈現(xiàn)為“水上漂萍”。這需要我們同時(shí)加強(qiáng)基礎(chǔ)研究的“對(duì)策”指向和對(duì)策研究的“基礎(chǔ)”意識(shí)。就藝術(shù)學(xué)對(duì)策研究的“問題”意識(shí)和“基礎(chǔ)”意識(shí)而言,我以為近年來《中國藝術(shù)報(bào)》給予了極大的關(guān)注并取得了顯著的成就。僅今年以來,就有顏榴《叩問國家美術(shù)館》(1月14日)、楊瑞慶《期盼戲曲新流派脫穎而出》(1月18日)、陳友軍《青春偶像劇中的“人”與“城”》(1月2日)、喬燕冰《能否詩意地棲居在自己的屋檐下》(2月4日)、趙勇《從搖滾到民謠:“批判現(xiàn)實(shí)”的音樂軌跡》(2月4日)、周思明《對(duì)當(dāng)前相聲的思考和諫言》(2月25日)、慕羽《中國音樂劇發(fā)展要樹立“多變目標(biāo)”》(3月4日)、劉厚生《建設(shè)社會(huì)主義文化強(qiáng)國,戲曲怎么辦?》(4月15日)、喬燕冰《中國舞者,為何難走出生存魔咒?》(4月17日)、汪人元《優(yōu)秀戲曲唱腔的“新”與“高”》(5月15日)、賈方舟《寫實(shí)主義在當(dāng)代的可能性》(5月29日)、劉星《中國民族管弦樂隊(duì)之思》(6月17日)、章旭清和付少武《西方“藝術(shù)終結(jié)論”對(duì)中國藝術(shù)發(fā)展的現(xiàn)代隱喻》(6月19日)等多篇佳作問世。可以認(rèn)為,關(guān)注對(duì)策研究不僅強(qiáng)化了《中國藝術(shù)報(bào)》對(duì)藝術(shù)學(xué)研究的針對(duì)性和有效性,而且極大地提升著該報(bào)的影響力和美譽(yù)度。
2.“問題意識(shí)”是時(shí)代的聲音并指向“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”
北京大學(xué)教授何懷宏出了一部“思辯集粹”的文集,書名就叫《問題意識(shí)》。書的“代序”是何懷宏在北京大學(xué)的一次演講,題為《問學(xué)之路》。講演中,他杜撰了一副對(duì)聯(lián)來區(qū)別“學(xué)術(shù)”與“學(xué)問”,聯(lián)曰:“學(xué)術(shù)是大家的,學(xué)術(shù)乃天下之公器,有規(guī)有界;學(xué)問是個(gè)人的,學(xué)問乃自我之心得,無端無涯”。他為這副對(duì)聯(lián)做的“橫批”叫“有學(xué)乃大”。這里的“學(xué)術(shù)”,即我們前述基礎(chǔ)研究的“學(xué)理”;這里的“學(xué)問”,也就是我們所說對(duì)策研究的“學(xué)識(shí)”。學(xué)術(shù)、學(xué)問關(guān)注的是過程,而學(xué)理、學(xué)識(shí)強(qiáng)調(diào)的是結(jié)果。在我看來,“學(xué)識(shí)”不僅是“學(xué)問”追求的產(chǎn)物,而且也是“學(xué)問”價(jià)值的支撐。因此我認(rèn)為,“學(xué)問”從“無端無涯”來說是“自我之心得”,但從“有用有效”來說也應(yīng)是“天下之公器”。
在何懷宏看來,“學(xué)術(shù)”首先是“學(xué)述”,即孔子自言“述而不作”的“述”。“述而不作”作為學(xué)術(shù),意在“以述代作”。當(dāng)然,要“述”得周全、述成系統(tǒng)、述出新意也并非易事。現(xiàn)在的“基礎(chǔ)研究”,當(dāng)然不會(huì)“述而不作”,其“有規(guī)有界”的方式是“先述后作”,也即馮友蘭所言先“照著說”再“接著說”。如果“對(duì)策研究”缺失,這種“接著說”恐怕只會(huì)是“照著說”的邏輯推演,而非基于“對(duì)策研究”成果之“看著說”的自覺修正。與“學(xué)術(shù)”不同,“學(xué)問”的本質(zhì)在于“問學(xué)”,也就是學(xué)由“問”起、學(xué)解“問”惑、學(xué)釋“問”疑。我們說“學(xué)問”既是“自我之心得”也應(yīng)是“天下之公器”,在于“對(duì)策研究”強(qiáng)調(diào)的“問題意識(shí)”是時(shí)代的聲音,應(yīng)對(duì)“問題意識(shí)”所指向的“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”是大眾的情懷。
何懷宏指出“學(xué)問”有“知識(shí)性的問”和“思想性的問”之分,前者如孔子的“子入太廟,每事問”,后者如蘇格拉底對(duì)知識(shí)“果真如此?”的詰問。我把這兩種“問”視為“求知之問”與“求真之問”。其實(shí),我倒愿意視這兩“問”為我們做“對(duì)策研究”的兩個(gè)步驟,即先“求知”再“求真”。只是在求知、求真之后,我們還要“求策”——求有針對(duì)性、講時(shí)效性的“應(yīng)對(duì)”之策,這個(gè)“求策”就是我們應(yīng)對(duì)“問題意識(shí)”所指向的“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”。鑒于對(duì)所求之策的“價(jià)值關(guān)懷”還會(huì)有“價(jià)值”評(píng)估與考量,我們對(duì)策研究的“問題意識(shí)”一不要“可憐夜半虛前席,不問蒼生問鬼神”,二不要“躲進(jìn)小樓成一統(tǒng),管他冬夏與春秋”。“問題意識(shí)”是時(shí)代的也是社會(huì)的。
(編輯:竹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