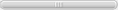溺亡的伊卡洛斯與維米爾的救贖
溺亡的伊卡洛斯與維米爾的救贖
——解讀《持酒杯的女孩》

持酒杯的女孩(布面油畫) 維米爾
“你的夢(mèng)境已至臻榮耀且終將燃盡”,因翅膀融化而溺亡深海的伊卡洛斯在無(wú)限接近太陽(yáng)時(shí)一定忘記了詩(shī)人的讖語(yǔ)。但在中國(guó)青花瓷瓶和波斯羊毛掛毯中盡享黃金時(shí)代、在最早的股票交易中坐地生財(cái)?shù)暮商m先民卻不敢忘記,他們將這個(gè)樂(lè)極生悲的年輕人鐫刻在阿姆斯特丹市政廳破產(chǎn)處的門楣上,讓過(guò)往于此的每一個(gè)人自問(wèn)自省。當(dāng)信仰型、風(fēng)俗型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被幾何增長(zhǎng)的貿(mào)易總量擊潰,資本與市場(chǎng)成為決定航向的舵輪,連一向陽(yáng)春白雪的藝術(shù)都把描繪對(duì)象鎖定為俗世生活的瑣細(xì)片段時(shí),對(duì)榮耀和享樂(lè)的過(guò)度沉迷是否會(huì)導(dǎo)致伊卡洛斯的悲劇最終降臨?在當(dāng)時(shí)的荷蘭,維米爾是對(duì)這種恐懼思考最深刻的藝術(shù)家,《持酒杯的女孩》則是直面這種憂慮的終結(jié)之作。
在《持酒杯的女孩》中,畫家用三道視線完成了對(duì)此焦慮的心靈闡釋和自我救贖。第一道視線來(lái)自敬酒求愛(ài)的男人,他的目光與右手都朝向持酒杯的女孩,最終指向交換的主題。欲望和引誘成為了消費(fèi)對(duì)象,軍官的海貍皮帽、女孩的綢緞華服、桌上的青花瓷器無(wú)不是財(cái)富、奢侈與享樂(lè)的縮影,這是符合風(fēng)俗畫描述習(xí)慣的極富挑逗意味的目光。第二道視線來(lái)自畫中畫里的人物,他從傳統(tǒng)道德的高度審視著這場(chǎng)交易。維米爾用早已丟棄的傳統(tǒng)肖像畫法將這一形象與“過(guò)時(shí)”的符號(hào)聯(lián)系在一起,借以拆穿道德說(shuō)教的偽裝。第三道目光是維米爾思考的核心,這是來(lái)自觀者的眼光。桌邊睡著的男人以旁觀者的身份和畫外受眾站在相同的立場(chǎng):一方面,他如頭頂畫中畫里的人物一樣,在暗中偷想著女孩;另一方面,男人用沉思的姿態(tài)關(guān)注著他身邊的交易,這又被窗戶上隱約出現(xiàn)的持韁繩的女神所印證——在荷蘭傳統(tǒng)神話中,持韁繩的女神代表對(duì)欲望的節(jié)制。
由此可見(jiàn),維米爾想要提供給觀者的三重評(píng)論視角:第一,是對(duì)社會(huì)現(xiàn)象的描述,人們已經(jīng)在財(cái)富與享樂(lè)中得意忘形;第二,是對(duì)道德教化的討論,紙迷金醉的市場(chǎng)型社會(huì)使傳統(tǒng)道德監(jiān)管日漸式微;第三,是通過(guò)空間配置完成的對(duì)個(gè)人反思維度的構(gòu)建,這就是維米爾的救贖。當(dāng)說(shuō)教并不足以指引人們避免伊卡洛斯的悲劇,用理性沉思代替盲目跟從成為獲救的唯一辦法。
至此,我們不難想到這幅作品誕生10余年前,在距離德夫特不遠(yuǎn)的阿姆斯特丹,笛卡爾的《第一哲學(xué)沉思》首次付梓,并由此開(kāi)啟了歐陸理性主義的先河。恰巧,笛卡爾的密友、顯微鏡的發(fā)明人雷文霍克不僅與維米爾是同鄉(xiāng),而且被維米爾選定為法定遺囑執(zhí)行人。在相同的時(shí)代和社會(huì)土壤中,確實(shí)孕育出了諸多彰顯理性的哲學(xué)、科學(xué)、技術(shù)和藝術(shù)成果。兩個(gè)世紀(jì)后,《追憶似水流年》中的作家伯戈特在臨死前做了關(guān)于維米爾畫中一小塊黃色顏料和信仰之間關(guān)系的著名論述。相信他命絕于畫前時(shí),一定讀懂了維米爾的救贖并因此而靈魂獲赦。
(編輯:竹子)